我们不是不知道,而是不敢知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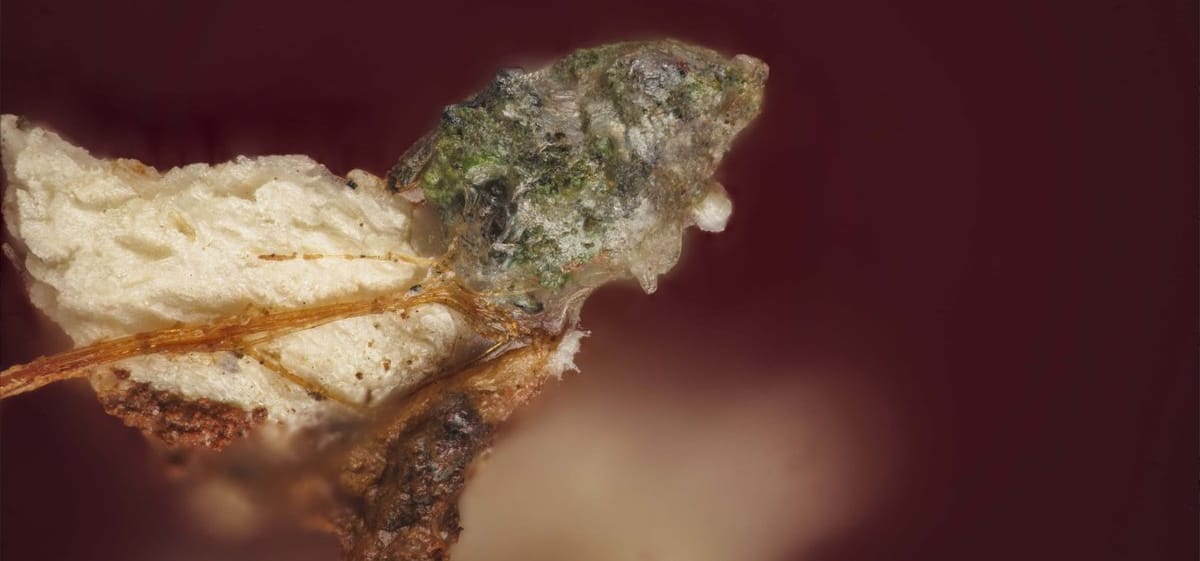
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与良渚街道的自来水出了问题,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了。但问题不只是出在水上,更出在回应的方式上:
- 7月16日上午9点,市民发现水有异味,开始打电话投诉;
- 整整12个小时,官方没有停水、没有预警、没有公告;
- 晚上21:44,自来水公司终于发布通知,却语焉不详、避重就轻,只说“水已达标”“可以放心饮用”,既不说明原因,也不承认责任。
这一切,看起来像是无能,像是混乱,甚至像是愚蠢。可真的只是这样吗?
别误会——这不是一群“平庸之人”在胡乱应对,而是中国体制内最聪明的一群人:
他们是从基层科层一路上来的业务骨干,是熟悉规则、擅长风险控制、精通上行报告语言的系统精英。
他们没有一个是傻子。正因为足够聪明,他们才深知:在一个讲究服从、讲究责任切割、讲究政治风险最小化的系统里,什么能说、什么不能做。
所以我很好奇:为什么这样一群人,在一个关系上百万人饮水安全的民生危机中,会集体做出一连串“显而易见的错误决定”?
明知最基本的应对逻辑是:停水、公告、道歉、调查、设置备用供水点,
但他们偏偏选择了沉默、拖延、模糊和删帖。
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是“正确”的做法吗?
他们太知道了。
但他们更清楚:正确意味着承担责任,而责任必须有代价。
于是,我写下这篇文章,试图站在他们的角度,解释:
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——
明明全员都很聪明,结果却如此愚蠢。
一、我们不是没察觉出事了,而是不敢承认
7月16日9点起,市民陆续投诉“水有异味”。
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“水出了什么问题”,而是:“情况会不会闹大?要不要报告?能不能先稳住?”
如果你理解这个体制,就不会觉得奇怪:
没有哪个干部敢主动宣布停水。
因为那意味着你“发现了问题”,
而问题一旦被确认,就必须有人“为问题负责”。
而你,就是那个“发现问题的人”。
在我们的系统里,发现问题的人,常常就是问题本身。
你可以指望工程师检查管道,但绝不能指望一位主任签字承认“水源污染严重”。
一旦盖章,就意味着:
市里要问你为什么没提前预警,省里要问你政治站位够不够高,纪委要问你有没有失职渎职。
我们不是不知道水臭,而是不敢说水臭。
你们以为应该第一时间停水、公告、设点供水,但你们不知道,
每一个决定都要对应责任划分、舆情备案、层层签字、责任追踪。
你只要走错一步,明天就成了问责通报里的名字。
所以我们做了最理性的选择:
- 假装没看见,等舆情自行扩散;
- 用“市民反映”代替“我们发现”;
- 不提污染源,只说“现已达标”;
- 通告时间尽量拖,最好熬过热搜窗口。
这不是懒政,这是自保。
二、我们最怕的,不是你骂我们,而是你太聪明
我们并不怕大家发泄不满,
我们怕的是:你说对了。
当有人晒出黄浊的水、变色的滤芯,有人翻出粪大肠杆菌的数据,有人怀疑水源污染来自上游德清,有人指出东苕溪水质多年来劣迹斑斑……
我们慌的不是“问题多严重”,而是“我们已经没办法解释”。
因为这些事,我们自己早知道了。
我们知道东苕溪是杭州水质最差的水源;
我们知道上游德清的养殖废水十几年没管彻底;
我们知道仁和、良渚喝不上千岛湖的水,是资源配置的现实;
我们甚至知道,6月底的监测报告中,粪大肠菌指标已经严重超标。
但这些,只能我们知道。
一旦你知道,就要问:你们为什么早知道,却什么都没做?
所以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处理掉“说出问题的人”。
我们不能承认水里可能有屎,但我们可以先抓“说水有屎”的人。
这就叫“维稳优先级”:
真相不重要,可控才重要。
三、我们不是没人负责,而是谁都不愿第一个被牺牲
很多人问:为什么市领导不说话?区委书记不露面?
是不是他们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?
不。他们当然知道。
但他们也知道:一旦你出面说话,就成了问责链条的起点。
哪怕你只是想道歉,也会被默认为“默认了责任”;
哪怕你只是想稳定局面,也会被怀疑“想主动背锅”。
在这个系统里,责任感不是美德,而是一种制度风险。
我们不是不负责,我们只是都太明白:
第一步错了,就走不回来了。
所以最稳妥的选择就是:
谁也别说,谁也别认,谁也别动。
等调查组下来、等通报发出、等风波过去,
自然就没人再问了。
这不是冷漠,这是“理性”。
四、我们不是不知道信任会崩塌,而是早就不指望它了
你说:你们这么做,不怕群众不信任了吗?
我们说实话:我们不靠“信任”维系运行。
我们靠的是组织稳定、层级通道、舆情管理和制度惯性。
你会继续用水,继续上缴费用,继续填调研问卷;
你再不信任,也不会有更有效的表达方式。
我们不怕你愤怒,只怕你“不可控”;
我们不怕你失望,只怕你“出圈扩散”;
你如果实在不满意,最多自费体检、换个城市生活,
但你换不掉的是这个逻辑。
对我们来说,只要上级没有追责,我们就是合格干部。
这不是事故,这是机制的逻辑终点
你可能会问,我们就不内疚吗?
偶尔会,深夜时会。
但白天还有报告、会议、通报、口径协调……
我们连愧疚的权利都没有。
而且我们真做错了吗?
不。我们只是做了这个系统教会我们做的一切:
- 程序正确
- 责任最小
- 上级满意
- 群众沉默
所以我们想说:
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,也不是哪一个部门的失职,
这是我们的集体智慧,是一整套制度,在逻辑自洽地运转。
当面对人民时,我们想的是怎么“应付”;
当面对上级时,我们想的是怎么“保住”;
当面对真相时,我们想的是怎么“润色”。
在这个系统里,做错事不会倒霉,承认错误才会。
如果你非要我们说“对不起”,我们可以说,
但别指望我们真的改变。
所以你看,
我们不是崩坏了,
我们只是运行得太符合逻辑。
一切都是对的,
除了结果。




